丹津 葩默——雪山閉關12年的西方比丘尼
发布时间:2019-11-08 10:21:39作者:药师经常识网丹津 葩默——雪山閉關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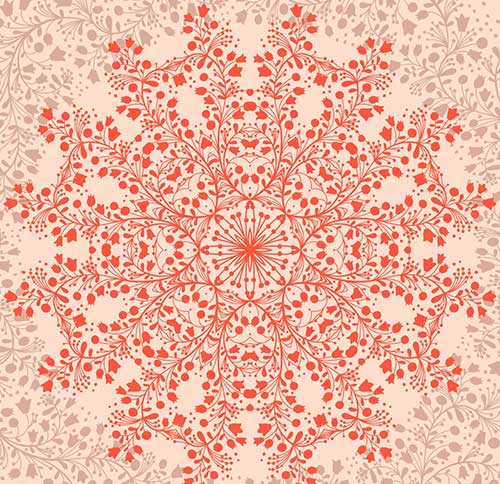
丹津 • 巴默出生及成長於倫敦, 18 歲皈依為佛教徒, 20 歲到印度 ,21 歲出家,在海拔一萬三千二百尺的喜馬拉雅山上的一個雪洞中 獨自一人修行了十二年,一次次面臨生死的考驗。 完成了不尋常的閉關修行,她的故事在西方世界早已成為一種傳奇, 由英國著名記者維琪 • 麥肯基執筆的《雪洞 : 喜馬拉 雅山上的悟道歷程》首次將這個關於信仰的傳奇故事介紹給中國讀者。 當被問到她這 12 年的閉關時 眼裡只有寧靜、善意和微笑的丹津葩默,如此總結她的雪穴閉關 12 年: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我從來不曾感覺無聊。 《雪洞》一書,會讓我們看到丹津 • 葩默( Tenzin Palmo )努力不懈的修行毅力! 閉關結束後,她開始了興建尼院和弘法利生的事業 《心湖上的倒影 : 給實修者的指導》是她經典演講合集。基於多年修行體悟,為我們闡釋了禪修中應對止觀、覺知與心性抱持的正確知見,釐清了佛教系統中上師、金剛乘與觀想的意義;並善於哂蒙鷦拥钠┯骱颓宄旱亩匆姡?蚱圃S多人對於禪修和佛教的錯誤觀念以及對生活的迷思,讓人們時刻保持覺知,以清明的心活在當下。 本文從諸多對她的介紹和她的演講中摘錄部分,對她的修行因緣和體悟做簡單的了解,從而對修行升起更加清晰的定解和信心,也對真正的修行者升起無比的敬意! 如果想對她進行更多的了解和認識,請大家閱讀《雪洞 : 喜馬拉雅山上的悟道歷程》和《心湖上的倒影 : 給實修者的指導》兩本書! 以下是她的部分演講自述: 前世因緣 (如果我是一位男人,事情會容易許多,因為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和仁波切住在一起。但是,因為我是一名女性,他們不太清楚要拿我怎麼辦。) 我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誕生於英國,並在倫敦長大。我的母親是一位通靈人,每週三晚間,我們家都會舉辦降靈會,也曾發生過桌子在房間裡飛來飛去這類的事情。我非常感激這樣的生長背景,因為這讓我從小就相信人死後意識會繼續存在。事實上,我們家經常談論死亡這個話題。所以,我對死亡從來沒有一點恐懼或不敢談論。 我想,我每天都在用某種方式思索死亡這件事,由於對死亡有所覺知,賦予我生命很大的意義。 十八歲時,對存在主義產生了興趣,我閱讀沙特和卡繆的作品。當時我在圖書館工作,有一天,碰巧拿到一本小書名為《不動搖的心》( The Mind Unshaken ),我很喜歡這個書名。作者是一位英國記者,敘述他在泰國的時光,書中描述最基本的佛法 四聖諦、八正道、三法印等。我仍然清楚記得這些多麼不同凡響的啟示,竟然有一條完美的道路,涵括了我所有的信念,簡直讓我心花怒放。 想到真的有一個宗教在教導這些道理,讓我非常震驚。我遇到的其它宗教,都安置了一個必要的神祇;相較之下,佛教是一條進入內在的道路,任何外在造物者或神的觀念全都是多餘的。這本書我才讀到一半就告訴母親:「我是個佛教徒。」 她說:「很好!親愛的。把書讀完,然後說給我聽。」六個月後,她也成為佛教徒。所有我讀過的書都一再強調,修行最重要的就是無欲。於是,我把衣服都送掉了,不再化妝,和男友分手,開始穿上一件黃色的衣服 那是一種古希臘及膝式寬大外衣,這是我所能找到最接近僧袍的衣服,然後穿黑色長襪。當時,我還沒有遇過任何佛教徒。我的母親非常有耐心,她什麼也沒有說。 大約過了六個月,我想:「或許我應該去找尋更多的佛教徒,我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位。」於是,我在電話簿裡的「佛教」一欄中尋找,發現了佛教團體。有一天我去那裡,發現佛教徒並沒有穿著古希臘式的寬大外衣晃來晃去,這些人都比我還早成為佛教徒,而且竟然穿著普通的衣服!女性甚至化妝並穿高跟鞋。之後,我對媽媽說:「把衣服都送走真可惜。」這時,她把衣櫃的鑰匙交給我,說:「你去看看。」我打開衣櫃,所有衣服都在裡面! 我相信我們來世間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那種屬於我們天生具有的圓滿特質。十八歲時,我讀到了一本有關佛教的書。 那是一本非常簡單的書,但我馬上知道這就是我一直所相信的東西。第一年左右,我是一個小乘的信徒,因為我喜歡小乘那種清淨、通達的氣質當時,我接觸的完全是南傳佛教。我和倫敦的錫蘭佛教寺廟十分親近。我喜歡南傳佛教的清楚明確,事實上,我愛它所有的一切。 當然,西方報導南傳佛教的方式和南傳佛教國家的情況不甚相同,在南傳佛教國家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西方很少有儀式,講究的是邏輯和清晰,而且很強調禪修,這讓我非常喜歡。我唯一不喜歡的是阿羅漢的觀念,阿羅漢似乎滿冷漠的,這使我感到憂慮,因為我已走上這條路,卻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喜歡它帶領的方向,我甚至問自己,究竟是不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當時是一九六 ○ 年代早期,倫敦大部分佛教徒都屬於南傳佛教。那時候還有一個所謂「韓佛瑞禪」( Humphries Zen )的現象,我指的當然是克里斯提思.韓佛瑞( Christies Humphries ),他自己發展出一套形式與眾不同的禪法。 當禪師到英國訪問他的禪中心時,他們目瞪口呆得說不出話來,於是,克里斯提思.韓佛瑞做了一個冗長的演說,然後轉向禪師問說:「現在你們想說些什麼嗎?」禪師通常回答:「我想你已經什麼都說了。」然後保持靜默。這就是當時我所能遇見的兩種佛教 韓佛瑞禪和南傳佛教。至於藏傳佛教在當時被視為有點像墮落的巫教,像一種邪法、古怪的性儀式,基本上它根本不被當成佛教,沒有人想和它有所牽扯,它被稱為喇嘛教。總之,它看起來非常的複雜和儀式化,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感覺自己似乎在這種佛教環境裡幾個世紀了,但其實只有一年左右,我的內心有好多東西在轉化。有一天我讀到一本佛教概論,書的結尾有一小篇談到藏傳佛教,它描述西藏有四大傳承。當我讀到「噶舉」這個名詞時,心裡有個聲音說:「你屬於噶舉。」而我說:「什麼是噶舉?」它說:「不要緊,你屬於噶舉。」我的心沉下去了。 我想:「噢!真是無法想像,不過人生本來就是這麼簡單,讓我來看看看現在發生什麼事了。」於是,我去見當地唯一對藏傳佛教有點了解的人(其實她的了解並不多),我對她說:「我想我屬於噶舉。」她說:「噢!你讀過《密勒日巴傳》嗎?」我回答:「誰是密勒日巴?」她把依凡.文茲( Evens Wentz )翻譯的《密勒日巴傳》遞給我。 離開之後,我讀了這本書,腦袋裡打了幾千個觔斗,它和我一向閱讀過的書都不一樣。最後,我終於了解自己果真是屬於噶舉。顯然,我必須找到一位老師。當時我閱讀許多經書,注意到只有比丘,從來沒有提到比丘尼,我感到點沮喪。然後有一天,我聽說在印度的達胡西市有一所噶舉派的尼院。 於是,我寫信給創辦者斐達.貝荻( Freda Bedi ),她是一位英國女士,非常令人驚嘆的人物。她嫁給一位在牛津大學遇見的印度人,並且在印度住了大約三十年,是印度自由邉拥囊环肿印K?m然是英國人,卻被英國人拘禁入獄。印度 duli 之後,她為印度政府做事,成為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甘地夫人的好友。之後她被派遣去幫助西藏難民,最後到了達胡西市,為年輕的轉世喇嘛創辦了一所學校,也創辦了一所尼院。我寫信給她,詢問是不是可以去那里和她一起工作。同時,我在英國遇見幾位喇嘛。 我在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工作,並且在那裡研習藏文。在這些喇嘛當中,有一位名叫丘揚.創巴( Chogyam Trungpa )的年輕轉世喇嘛,他和阿岡仁波切( Akong Rinpoche )一同來這裡,他們都在牛津大學讀書。 與上師 重逢 當時是一九六二到六三年,英國很少有人對藏傳佛教感興趣。所以,每當我們遇見創巴仁波切並問他:下次什麼時候見面?」他都是說:「下個週末。」一個週末他來,下個週末我們去,他的朋友很少,有一天他說:「你可能很難相信我在西藏是地位相當高的喇嘛,我從來沒有想到會落到這種地步。請問,我是不是可以教你禪修?我至少必須有一個弟子。」我說:「當然好啊。」 但是我還是想到印度旅行,也得到他的鼓勵。二十歲的我乘船到了印度,這是一趟非常愉快的旅行。我前往達胡西市,為斐達.貝荻的年輕喇嘛家庭學校工作。這是我第一次遇見梭巴喇嘛(喇嘛 Zopa )的地方,他是住在那裡的年輕轉世喇嘛之一。我住在尼院,擔任斐達.貝荻的秘書。有一天,我們收到一封信,提及西藏難民以手工製造的紙,問我們是不是能夠找到市場,這封信署名「坎初仁波切」( Khamtrul Rinpoche )。我一讀到這個名字,信心油然而生,就像書中所描述的那樣。第二天,我問斐達.貝荻:「坎初仁波切是誰?」她回答:「他是竹巴噶舉派的高僧。事實上,他是我們正在等待的一位喇嘛。」 知道我們在等待某位喇嘛,並已為他租了一間小屋,他將在夏季光臨。我問:「他是噶舉派的?」她說:「對。」我說:「那麼我可以皈依他。」她說:「對,對,他是一位很好的喇嘛。他來的時候,你一定要請教他。」當時是五月初,我們等了一整個五月,又等了六月一整個月。 六月最後一天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由於是滿月的日子,剛好有位喇嘛正在舉行長壽法會。忽然,電話鈴聲響起,斐達.貝荻接了,她放下電話說:「你最好的生日禮物剛剛到了公車站。」 我嚇壞了,我的上師終於來了。我跑回尼院,換上西藏長袍,拿了一條哈達 表達恭敬的白色長巾。然後,又跑回租來的房子,告訴他們仁波切來了,趕快準備。當我回到學校時,他已經到了。我記得自己幾乎是爬進房屋的,我害怕得不敢看他。我不知道他長得什麼模樣,連照片都沒有看過,他是老?年輕?胖?瘦?我一點概念也沒有,我只看見他袍服的下擺,還有他的咖啡色鞋子。我對這雙咖啡鞋做大禮拜,然後坐下來。 斐達.貝荻說話了:「這位是某某,她是佛教社的一員。」然後我對她說:「告訴他我想皈依。」於是她說:「噢!對。她希望皈依你。」仁波切說:「當然。」他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在說:「她當然想皈依,還有其它什麼是她想要的?」當我聽他用這種音調說「當然」時,我抬起頭時,第一次看見他。我看著他時,似乎有兩件事同時發生了,有一絲認識的感覺,好像遇到一位許久不見的老友;同時,我內心裡最深的東西好像忽然化為外在的形象了。 如果我是一位男人,事情會容易許多,因為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和仁波切住在一起。但是,因為我是一名女性,他們不太清楚要拿我怎麼辦。有一次,仁波切對我說:「從前我總能把你留在我的身邊,但是在這一世裡,你變成了女人,所以我只能盡力而為,不過我沒有辦法永遠讓你留在我身邊,因為這是很困難的。」他真的是盡力了。 過了六年,僧團遷到目前在扎西宗的地點,位於坎格拉山谷,距離達蘭色拉市大約三個小時的路程。遷居三個月後,坎初仁波切對我說:「現在是你離開去修行的時候了。」 心靈導師的角色 我對所有聲稱自己已經開悟的人都非常懷疑。我見過的所有西藏喇嘛,他們連做夢都不敢做這種聲明,大部分喇嘛會說:「噢!我和你一樣,我也在修行,也在訓練自己。在那邊的某某喇嘛,他非常棒,他是不同凡響的,他能做這、做那,但是我呢,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但這並不表示當他們坐在寶座上,就不能展現出內在的信心,信心應該來自他們的教導,而不是自我的擴張。我認為還有一件事必須注意,那就是當他們從寶座下來後,和一般人相處的情況。他們在一般環境裡的舉止怎麼樣?他們如何對待沒有利益關係的人們? 嘉華喇嘛說應該檢驗老師,我知道這很困難,尤其西方人經常過度信任和輕易相信老師,亞洲人的態度則嚴厲多了。他們有衡量的標準,因為他們經年累月處於修行的場合中。 西藏人並不天真,有些人以為西藏人頭腦簡單又迷信,但是西方人容易受騙的個性才讓西藏人目瞪口呆。西藏經本說,人們應該考驗老師十二年,才決定是不是要接受他。觀音上師甚至說,我們應該偵察上師!當他們不在眾人注目下的行為如何?是不是和藹又慈悲,或者根本是隨波逐流、享受好時光、喜歡收弟子?當我詢問我的上師某些在西方相當具爭議性的喇嘛,他說:「嗯!在那種情況下是很難評斷的,但是在這二十年內,觀察一下他們的弟子。」 這是看出老師程度到底如何非常好的指標,他的資深弟子情況怎麼樣?我們是不是希望像他們一樣?這位上師身邊的狀況如何?這種心態是不是健康?這些弟子是不是被操縱?他們如果不隨時奔向上師,是不是就沒有能力為自己做決定?他們是不是在心理上依賴自己的老師? 老師就如同母親一般的教育弟子。 西藏文的「喇嘛」,其實意指「位高的母親」,「嘛」( ma )字當然是女性,所以,喇嘛是女性的字眼,但西藏人平常不提這點。上師如同母親,當兒女都還年幼時,母親照顧、養育、愛護、規範、訓練他們,這是她的角色;小孩依賴母親,因為他們什麼都還不懂。但是,如果孩子已經長大,母親仍然希望當「媽咪」,希望孩子倚賴她,和她的圍裙帶連在一起,那麼她就不再是個好母親了。 一位好母親把孩子帶大,讓他們愈來愈獨立,成年時能夠離開家。一位好母親能養育孩子成為自主的生命,並在未來也成為他人的父母。同樣的,一位真正的上師能夠訓練弟子找到內心的智慧和內在的上師,訓練弟子替自己做決定。任何一位「上師」如果只是創造出一群崇拜他的侍者,等待他每一句如甘露般的話語,愈來愈倚賴他,並專注在滿足他所有的願望上,那麼這位上師只是愛上了「當上師」的想法。失去了弟子,這個人再也不是上師,弟子只是他權力的來源。這是一種權力的遊戲,使得人們即使不想做某種事,當你交代他們去做,他們就毫不懷疑地去做了,它會變成麻醉藥。 你可以在一些老師身邊看到這類事情的發生,年復一年,他們創造出這種共生的關係,弟子在這種環境裡更加倚賴上師。如果他們不先去覲見上師聽取他的說法,就什麼決定都不能做;如果真是如此,那便是錯得離譜。開始的時候,一位好老師當然會告訴弟子應該做什麼,因為他是指導者;但是一天天過去,老師開始會說:「好吧!你想要做什麼?你覺得自己現在應該做什麼?」上師漸漸將球丟回給弟子,讓弟子成長。當時機來臨時,上師可能乾脆把弟子送走。 十一世紀西藏的偉大瑜伽士密勒日巴,把弟子留在身邊,或在同一個洞穴,或在鄰近洞穴,直到他們的修行穩定了。然後,他就把弟子送走,卻不時去探訪他們,看他們的進度如何。上師應該幫助我們發現內在的智慧,讓我們不需要無止境的倚賴他的建議。可是,我們必須先做好自己的功課,淨化和簡化自己的心,讓心愈來愈廣闊。然後,當我們遇見上師,透過完全的專注,就能真正的接受傳法。 任何使我們學習的人就是老師 但是,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在西方,身邊的老師不多。我所到之處,經常被問到的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對治憤怒,另一個便是如何尋找老師,兩個問題都非常複雜。老師有許多種,有一種是以心相連的老師,他誓願帶領弟子在今生或來世得到開悟。 這是老師和弟子兩者都發的願,徹底的承諾,弟子需要完全的奉獻,所以,必須非常的小心。如果找到真正的上師,這是你今生修道中最大的福氣;如果你找到一位假的上師,那麼,套用西藏人的說法,老師和學生手牽手一起跳進深坑。依照西藏人的看法,你會下地獄。除了以心相連的上師,還有其它許多的老師。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每次遇見一位自己喜歡並覺得有關聯的老師,就要五體投地的說:「好,接受我,從今起直到開悟,我都屬於你。」 現在,我們在這裡,我們想回家,從無比的混亂回到自己最單純的真正本性。有許多人能幫我們上路,許多人能指示路標,那不必都是最根本的上師。任何能給我們正確幫助和指導的人,就是老師。他們可能以指導老師的身分出現,或者僅是一種短暫的相遇,甚至可能以親戚或朋友的形態出現,我們又怎麼會知道呢?任何使我們學習的人就是老師,就是心靈的朋友,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注意力從尋找心連心的上師,轉移到尋找心靈的朋友。 如果我們視老師為心靈的朋友,範圍就擴大了,因為我們可以有許多心靈朋友。佛陀曾說以法為師,而法就在這裡 方法就在這裡,修行就在這裡,這裡有修行多年而將生命奉獻給修行的人,許多懂得的人就在身邊,我們隨時可以得到幫助。這個人不一定以位高的心靈大師形態出現,散放出光芒,或事前發送小冊子,告訴所有人他們是開悟者。老師可能以非常簡單的形態出現,但是,如果他們有修行,有合格的老師,屬於純正的傳承並修行有成,他們就是合格的老師。 我們都有許多功課要做,必須多淨化,多學習如何平靜心、如何清淨心、如何簡化並了解心。不必一定要佛陀站在面前,我們只要依照指導,靠自己就能夠做到。光只是等待完美上師的出現是沒有用的,如我前面所說的,即使完美上師出現了,我們準備好了沒有?所以,現在就要做準備,有許多事情可做。然後,或許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就能引發重大的突破。 許多禪宗的故事,描述一些隱士住在某地,有些僧人云遊經過,隱士吐出一些謎語似的句子,這個僧人就「得道」了!但是他們不說得到什麼,因為在亞洲人心中,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位僧人遇見這位傳達謎語的某人之前,已經靜坐了三十年。它不只是一句話而已,但是當我們讀到這句話時想著:「這又怎麼樣?」它無法使我們大徹大悟。關鍵在於準備,所有那些無止境的、多少小時、多少年月的靜坐,在所有動作中保持覺照,真正學習如何把心準備好、訓練好而活在當下。你懂嗎?它不全來自上師,大部分必須來自弟子。 避免捲入對上師熱烈的追隨 許多故事敘述大成就者的生平事蹟,他們是第八、九世紀印度的偉大瑜伽士,通常是在家人,理髮匠、店主、珠寶商 各種不同行業的人們,他們發現自己處於某種精神困境中,找不到出路。然後有一位大師出現,給他們些微的教導 只是一些小方法,之後大師就離開了,再也沒有見面。但是,這些人練習這個方法,接受它,並將它轉化融入每日的生活中,直到他們獲得大成就。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和上師同住,或許只見過上師一次,但是他們努力修法,日復一日持續地修,直到得到成果。 所以,有時候尋找完美上師的理想,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怠惰,「嗯!我沒有成就,因為我還沒有找到老師。」但是,我們眼前已經有一切可做的事情。就像我前面說的,我們真正在做的,其實是重新和自己早已擁有的東西連結,並找到內在的上師,讓我們和自己原始的本性(智慧心)重新連結,它永遠都在那裡。最後,修行就是我們的皈依。 這或許不是身為藏傳佛教徒的我應該說的話,但說老實話,如果只是圍著上師團團轉,花費所有時間競爭地位,確定喇嘛注意到我們,這和法並不相干。它只是世俗情感的老套:得和失、樂和悲、譽和毀、好名和惡名。你可以在一些喇嘛身邊清楚看見這些事情,那裡有激烈的嫉妒和競爭。還不如回家坐在蒲團上,善待自己的家人,以他們做為自己的修行;還不如學習如何愛人、慈悲、和藹,耐心對待所有遇見的人。 通常,當人們捲入對上師的熱烈追隨,最後只為這個組織服務,視野會變得非常狹窄。他們眼中只有這位上師以及上師的僧團、組織和教導,其它都不存在了。如果你對自己加入的某個團體有所懷疑,不妨好好觀察一下那裡的人們,他們看起來是不是比你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更覺醒? 我相信能遇見真正有智慧的老師是最好的,因為他們具備非常特殊的氣度,這是所有傳承的一些喇嘛和老師們都具有的。當你和一位純正的大師在一起,你可以感受某種廣大、無我的特質,他不是一個只喜歡推銷自我的人。這位老師完全單純,但是當你和他在一起時,卻能夠體驗到某種特別的東西。當你遇見這樣的老師時,你應該從他那裡獲得一些教導,然後離開,好好下番功夫。如果目前你還沒有遇見像這樣的人,就從身邊任何來源的知識、智能和純正的修行里學習。我們都有許多功課要做,可以從現在開始做,四處遊蕩等待是一無所獲的! 「獨一無二的上師」的觀念是有害的,它讓人觀念完全混淆顛倒。我有一個完美的上師,我不是酸葡萄心理,但是我出自真心,不認為這是你們真正需要的,我們需要更多的修行,不是尋找香格里拉式的幻想。在電影《嘉瓦的一生》( Kundun )裡有一句很棒的台詞,嘉瓦喇嘛說: 譚將軍,你沒有辦法解放我,只有我能解放自己。 佛陀說,佛只指出道路,每個人必須自己上路。這似乎又有點矛盾,因為當我們遇見一位真正完美的大師,他確實能夠加速我們的進步,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巧遇見一位這樣完美的大師,太好了!但眼前之計,你只要好好修行,不要晃蕩等待,不要把你的整個生命建構在圍繞上師的場面上,這是非常浪費時間的事。 根據我的觀察,這些場面把我們非常根本的人性引發出來,卻沒有把它調和安定。有些上師變得毫無節制,我個人認為他們會走上極端。慈悲在哪裡?善巧的方法在哪裡? 人們變得非常困惑,只好告訴自己:「這必定是一種教導的方法。」它有點像:「更用力點打我!啊喲!好痛!這一定對我有好處。」或許這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或許它只是把你弄得瘀青!當然,情況不都是這樣,有些上師確實帶來很好的景象,但是,人們還是經常把能量放在熱烈圍繞上師上,沒有做內觀和自我覺察。我們最好專心保持生活的樸實,和自己的修行融合,不要被其它這些事情纏住了。 具備智慧,我們都是自己的上師 一位善巧的上師好比良好的外科醫生,他知道如何把手術刀放在正確的地方,身體雖然痛了一下,但卻得到治療,確實痊癒了。相反的,一位不善巧的外科醫生盲目地亂戳,碰觸不到要害,這種醫生會讓病人被切割、流血、留疤。開刀的目的不是製造痛苦,外科醫生必須找得到要害,讓病人得到醫療和轉化。 分析到最後,我們都是自己的上師,終須接觸自己內在的智慧。這可能有點危險,因為我們的心可能說的是自己想听的東西。但如果它教我們做的,正是自己不想做的事,那它就真的是內在嚮導! 我們都具備內在的智慧,我們應該更常和它接觸;然後,就會開始經驗到一種內心的平靜和自主的感覺。畢竟我們在努力追求成長,不要永遠做小孩。佛陀稱呼沒有開悟的人為「這些孩子」,有時它被翻譯為「愚人」,但那不是真的代表愚笨的人,那是指還不成熟的人。所以,我們這些已經修行一段時間的人,應該回顧一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們感覺內心真的有些轉變嗎?我們是不是真的開始長大了?我們是不是獲得更深的了悟?我們的內心生活是不是變得更清明單純和開闊廣大?我們的負面情緒,貪婪和慾望、憤怒和厭惡、幻覺和困惑,它們是消失、增加,還是依然如故? 十一世紀住在西藏的孟加拉國偉大聖人阿底峽曾說,測試修行有沒有成就的方法就是,觀看我們的負面情緒是不是消減了。如果不是,那就是沒有用的;如果是,就知道自己沒有走錯路。我們都可以自己做測驗,不需要其它人告訴我們。道路在這裡,已經有非常多的文字描述,很多人走過這條路,他們和我們同在,我們不必放棄一切跑到印度,修行的地方就在此時此地,與我們的家人、工作、社會責任同在。如果沒有辦法在這裡修行,那要到什麼地方去修?我們帶著自己的心四處走,在里斯摩( Lismore )的心和在喜瑪拉雅山的心是一樣的,同樣的自我、同樣的問題,何必去喜瑪拉雅山?為什麼不在此時此地解決它?沒有一位大師能代替我們做,沒有一位大師能消除我們的貪婪、憤怒和嫉妒,沒有一位大師能除掉我們的自我 每個人必須自己做到。






